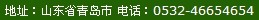|
北京中科白殿疯医院在哪 https://news.360xh.com/202003/23/56277.html 怀乡起义前后的回忆 作者:杨一士(万元) 文字:个阅读约25分钟 一、播种。 从北京发起的“五四”运动,逐渐影响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这时候信宜县在广州市读书的学生纷纷在暑假期间提前回乡宣传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后来,“五卅”运动兴起,接着就是“六·二三”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革命浪潮波及信宜中学、怀新小学等校,激发了学校师生的革命热情。怀乡圩镇地处于一个交通不大方便的山区,东西横亘的黄华江,可以行船和放木筏竹筏,新图地区许多竹、木、松、杉、茶叶、春砂、蓝靛、山楂、黑榄等山货可从蓝村、官渡头等地起运直放梧州、广州,商业和手工业仅次于镇隆和东镇,文化也不算落后,有不少青年到广州和高州求学,当时的罗克明、高君策就是赴省学习的大学生,张敏豪、张树年、陈文炎、丘国宗等一批青年到高州读书。在那里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共青团或青年社。当时身为国民党南路特委领导人的我党党员黄学增和朱也赤、王克欧等同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外出就学的青年返回怀乡时,就自动地上圩,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影响很大。 二、农运与青运 一九二六年开始,中共南路特委派王克欧同志来怀乡组织农会。王克欧是潮汕人(别字王皓明),记得他是带领留高州的学生张树年、陈文炎、张信豪、张敏豪来怀乡开展农运的。留省学生,则有共产党员罗克明、高君策,他们是直接由省委派来怀乡搞农运的。南路特委朱也赤同志也经常来怀乡搞农会。因此,在信宜来说,怀乡的农会组织得比较早。 但是最初的怀乡区农会组织,只不过是一个招牌,设在怀乡圩商会里,商会会长曾是张俊民,他是张树年的父亲。开头农民参加农会还是很少,农会是公开的组织,因而连高建侯这个政客也混了进来。当时怀新小学校长罗xx、教员张翊民是共产党员,学生到高建侯家去宣传、食宿,把他当开明士绅看待。随着革命的逐步深入,政治形势也不断地变化,当蒋介石夺了国民党的大权时,高建侯就走向反动了。 当年怀乡起义指挥部 我在信宜中学第一学期,学习成绩好,追求进步,陈其昌就吸收我参加共青团的组织。从此,我常常跟着学生会去搞宣传工作。 当时,信宜中学校内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颇尖锐,有个教师叫余子超。他教《三民主义》、《科学概论》,兼县教育科长或职员。他反对农运,干涉怀乡农会借用新图义仓谷(奖学金)作经费,于是怀乡区农会就派高君策(广州法政专科学校学生)去信宜新图学会同余于超斗争,婴他收回成命。会议在夜间开,斗得余子超面红耳赤。 在国共合作期间,学运和农运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六年冬我们团员搞了一次反对林云陔运动。这次是梁承枢(信中毕业生,共青团员)指挥我们团员回家乡去找乡长签名反对林云陔的,我回到榕垌找杨泽庭,说明林云陔压迫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我们要反对他,杨泽庭说:“林云陔是有名气的人物,我不敢反对。”其他的团员也没有签到名。可见当时的乡长、乡绅都是拥护有权势的林云陔的。 潘汉文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信宜县党部的执委。他在中学很活跃,是信宜学生会会长。学生会经常运来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进步杂志,如《向导》周报、《少年先锋》半月刊,马克思的《工钱、劳动和资本》、《价值、价格和利润》和《资本论浅说》、《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彭述之的《共产主义间答》。这些书刊对我们思想犹如旱天的霹雳雷声,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比看《新青年》和《独秀文存》又有进一步的启发。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信仰。 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每次传来胜利消息时,信宜中学革命师生成群结队游行庆祝。学生会还组织学生下乡向农民宣传,扩大影响。 中共南路特委书记黄学增同志、委员钟竹筠(女)同志经常来信宜做革命工作。黄学增同志以国民党的名义作公开的活动。他对学生、群众讲话,对党团员讲话,总是娓娓动听,深入人心。他教我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歌、农民苦歌。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师生讲话,首先讲革命形势的发展,其次讲学生对革命应有的责任,号召要为实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说:“信宜的农民是有革命传统的,辛亥革命之前,洪门会农民支持了辛亥革命,许多信宜人在广州当兵也支持了辛亥革命运动。洪门会是反清复明的组织,他们在长江一带支持辛亥革命。信宜洪门会,潜伏在农民群众之中,信宜新图位于山区,农民经常起来抗捐抗税,致使官兵不敢入新图地区收税。这种抗捐抗税,是农民的自发的革命运动。我们应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参加革命,为反帝反封建反地主土豪劣绅而斗争。”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罗克明同忠到信宜中学演讲。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县委书记。罗克明同志曾在高州中学毕业,在怀新小学任过教师,以后到广东国民大学学习。他在信宜中学演讲时,揭露当时国民党右派破坏信宜农民运动的罪恶,大声疾呼要同这些坏蛋作斗争,他指出:“信宜还有少数跳梁小丑,企国压迫怀乡区农会,怀乡区农会的农民群众非常愤怒,个个磨拳擦掌,要大兴问罪之师,把那些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走狗、压迫七区农会的凶手拉出来枪决!” 三、怀乡起义前夕 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形势起了变化,留在高州的学生中的共青团员纷纷回老家了,刘美昶、张信豪、张树年、陈文炎、张敏豪、刘克家、孔昭然、孔昭俊都返回家乡。信宜中学的团员债怒评击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校长刘力臣、学生会长潘汉文,造成学校工作瘫痪,这样全体学生一哄而散了。新图的学生和共青团员陈其新、陈其昌、杨万元、张凯如、杨廷焕、叶大华、陈鸿耀也回到怀乡。怀乡的革命青年也就多起来了。 这时候南路特委朱也赤来到怀乡担任领导工作,罗克明同志也回到怀乡担任信宜县委书记。王克欧、张树年、陈文炎去广州做工作,怀乡农会由朱也赤、罗克明两同志接办。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罗克明同志带同省委委员潘考鉴来到怀乡,他们乘海轮到水东,然后走陆路来信宜的。罗、潘两人刚到,当晚就在怀新小学后院的大教室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上百人。隔壁就是区公署,但我们党团不把区长周植盛放在眼里。会议是由罗克明主持,潘考鉴作政治报告,传达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情况和“八七”会议的精神。罗克明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了组织武装的问题,表扬了杨万禄交出一支枪,还说对帮会中的人物,要团员去做他们的工作,发动他们参加革命,一人参加就多一枝枪,一队参加就多一批枪。朱也赤同志也讲了关于军运的情况:茶山、牛蕴、怀乡、扶龙都有帮会的同志参加革命。远一点的如钱排、达国、分界这些地方也有大批人马。近处的较容易掌握,远处的就有相机而动的思想。另外,叶雪松参加到我们的队伍来了,叶雪松是带过军队的,解散了,还留下有一些枪枝,他可能支持我们,这是我们在怀乡地区的武装队伍,凑合起来就根当可观。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拿得出米的。问题还在于粮饷问题。 在广州起义前夕,由于王克欧、张树年、陈文炎等同志调去广州参加革命工作,信宜县党团县委作了重新安排。县委是朱也赤(兼)罗克明、业之,罗克明为书记。县团委是张敏豪(书记)、杨万元(宣传)、罗翘英(组织)。 党团县委还动员所有的团员返回信宜中学学习,布置两个由湛江到怀乡的交通员跟我联络。城内有一个曾是信宜中学毕业的梁承枢,他住在天飞街,跟交通员和信宜中学联系。我们在学校掀起了声援并要求释放潘汉文和刘力臣的运动。刘力臣是国民党左派,曾支持我们党团的革命工作,所以要营教他,通过营救工作来争取革命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不久,潘、刘被释放)。党团县委还决定我兼任信宜中学团组织的书记。 我们团员回到信宜中学,校长已经换上林树x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学校地理老师梁荃生奉命改组全县的学生会,我团组织同他们斗争,选举的结果团员占多数,梁荃生的反革命面目暴露了,他口嚷要把新图学生代表删掉。 团组织召集了一次全校团员大会,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便组织星期日旅行。大家步行到茂名宝圩附近开会,由我传达了潘考鉴报告的精神,团员得到了鼓舞。为了及时汇报情况,我经常在星期六下午上东镇,连夜步行返怀乡汇报信中革命斗争情况,请示今后的工作。 有一次朱也赤和罗克明同志从广州湾回到怀乡,朱也赤同志传达了上级党的负责人到广州湾策划怀乡起义的计划。朱也赤同志说:“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策动广州暴动,在此同时进行海陆丰暴动、信宜怀乡暴动、海南岛文昌暴动。信宜怀乡的暴动,就是依靠贫农、雇农、失业农民、帮会武装、学生队伍,以及国民党左派等政治力量,我们要准备好,通过交通员的联络,约定一定时间,一呼百应,义无返顾。首先要把部队整编好,编好军队的组织,十人一班,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三连一营,三营一团。到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着黑夜,夺取区公署的枪支。投降的反动军队,愿意跟随的跟随,不愿的释放归家,主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罗克明同志结合到怀乡最近活动情况说:“组织武装,必须宣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豪绅,分配他们的土地,农民认识到有土地分配,才会愿意参加革命。信宜有优良的条件,信宜新图地方,农民贫穷破产,有许多人到南洋做猪仔,被人拐骗卖到南洋各地做工。可见失业农民很多,对他们要加强宣传,把他们组织起来。” 四、革命暴动 十二月十五日,当日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信宜中学全体青年团员,当夜赶到怀乡参加怀乡起义。当时随我回怀乡的有杨廷焕、张凯如等人。我们回到怀乡圩头时,看见第二区署门前聚集许多人,大门旁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广东省信宜县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怀新小学许多同学迎着我们进内,看见朱也赤、罗克明同志以及许多穿着便装的武装人员。朱、罗两同志告诉我们昨晚十一、二点钟左右举行起义的消息。罗克明同志说,这次为了配合广州起义,发动了怀乡起义,昨日晚上由朱也赤同志指挥,从怀新小学集合出发。当晚反动区长周植盛与若干豪件在圩头团局打麻雀牌。团局是豪绅们的俱乐部,有的在那里吸鸦片烟,有的在打麻雀牌。团局大门口有岗哨。朱也赤问志打前锋,他拔开手枪,带领部队冲了进去,枪口指着周植盛,吓得其他豪绅抱头鼠窜,有的越窗逃出,有的率入庙外的字纸炉、簕林去。我们押着周植盛回二区公署,强令他叫开大门。当大门打开时,朱也赤同志说,缴枪不杀,守卫的规规矩矩,两只手举得高高的,警兵一个个的投降了。我们把周植盛关在大客厅的右厢房内,他卧室的鸦片、烟枪全被销毁。 介绍起义经过后,罗克明同志叫我带宣传队上街宣传,我就和宣传队到圩尾张家祠门前广场演讲,当时来听的人真是人山人海。 当天晚上罗克明同志诚我到县城拍电报给高州杨芝芬(注:杨芝芬是高雷警备区司令部的主任),并即日赶到高州同杨芝芬联系。我拍完电报后,当日步行九十里路赶到高州,找到杨芝芬,谈了情况,杨芝芬答应在我们攻打高州时响应我们。第二天我急赶回信宜,信宜县城门半掩着,气氛很紧张。 在我离开怀乡当天晚上,反动区长周植盛暗中同他的旧部属眉来眼去,心谋不轨。因此,县委决定枪决他,由罗翘英、杨万禄执行枪决。 我回到怀乡时,朱也赤同志已去分界联系军队。我向罗克明同志汇报了高州的情况。罗克明同志叫我马上到钱排圩找凌肖和,告诉他怀乡起义消息,要他立刻开拔。我到钱排找到凌时,他说:军队一出动,就要吃饭,必须有开拔费才行。”因为没有开拔费,我只好赶回怀乡。这时候罗克明同志正在考虑整顿红军和赤卫队的问题,把有战斗经验的成年编为红军,没有战斗经验的编为赤卫队,交给我们县团委指挥赤卫队的任务。因为广州暴动失败,人心涣散,阿吵佬、张少平、杨花旦、丘华标(注:帮会土匪人物)等都纷纷请求回家去。 国民党反动派向我们反扑,怀乡司令部的牌子也取下来了。随即我党贴出了一张通告,说明我们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暂时转入山区,再次宣传我们要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国民党反动派信宜县长杨伟绩被赶走之后又复职了,遇行了极凶暴残忍的反扑,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趁机竭力搜索敲诈,发了横财。记得我的中国公学的同学吴锡霖普经说过,杨伟绩第二次上台做县长,刮前民脂民膏达数以万计的银元,为信宜县历史上县长贪污之罪恶之最大者。为了搜捕革命同志,叶雷松、朱也赤、罗克明、各悬赏千元,杨万元、杨万禄、罗翘英、张信豫、张敏豪、刘君勉、刘克家(父子)等各悬赏五百元,并用十家联结方法来搞白色恐怖。 五、转移 怀乡起义失败后,县委领导认为整个新图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于是转入山区组织装武力量,重点在达垌。撤出怀乡后,要加强交通联系,杨叙庆是一个好交通员,人生得矮细,出入没人注意,身体很结实,走路很快,日行百里,不知疲劳,罗克明同志说:“杨叙庆同志是我们的优秀交通员,他服从命令,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们同志间的联系就靠他来干。” 罗克明进入达垌不久,通知我到达垌某农家找他,并要设法筹三十元钱出。为了这事,我父亲卖掉一头牛犊子支持革命。我到达垌后,那里的农民知道广州起义失败,有点犹豫,使组织装武工作遇到困难。于是,罗克明同志和我一同到分界找朱也赤同志研究局势。另外,布置张敏豪、张信豪去怀乡、扶龙同张少平、罗成进、阿吵佬等帮门头子联络。 我们到分界找到朱也赤同志,那里搞军事也有许多困难。大家商量研究之后,决定罗克明同志和我到林垌去活动“张大哥”,“张大哥”是林垌的帮会的有势力者。我们在林垌住了几天,局面不能打开。“张大哥”态度也很模糊,总是问我们全国形势、全省形势、全信宜县形势怎样,更关心的问我们有多少钱。关于钱的问题,这是当时我们搞军运面临的重大困难,甚至连我们吃饭也成问题。我从家里带来的三十元已经用完了,罗克明同志对“张大哥”讲了苏联的强大,帝国主义的经济衰颓,新旧军网的混战,人民生活的日趋困难,农民迫切要求土地的形势,然后说:“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信宜怀乡起义,暂时上山,实则重整队伍,只要把队伍组织起来,不难东山再起,信宜、罗定(罗镜、分界、钱排、达垌、合水、怀乡、茶山、云开、林垌等地)联合起来,纵横云开大山脉,出没无常,农民入则为农,出则为军,一面耕种。一面干革命,一定可以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 罗克明这样一讲,讲得“张大哥”有点心动了,他最后说:“你们回去吧,我有朝一日,就要和共产党一起作战跟着罗大哥走!" 我们离开“张大哥”,出到林调口的时候,再一次鉴赏石印庙一带大好的景色。林垌的河水不小,但流到林垌口的时候,突被一道石岩拦住,全流的河水从石岩底下流出,形成一个很大的旋涡。罗克明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在信宜怀乡建立苏维埃政府,如能在林垌建立苏维埃政府、出没信罗两县,必能吸引云开大山脉的所有农民的向往,为革命事业开展广阔的道路。” 我们回到分界,向朱也赤汇报了情况,朱也赤说:“我到林垌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搞得成第二次怀乡起义,就有可能得林垌“张大哥”的一支力量的帮动。”朱也赤同志因而问我:“你在分界附近有无亲成朋友,可请他出一把力的呢?" 我说:“我有一个堂姐姐嫁到罗镜圩。那里就是蔡廷锴出生地,也是他起家的地方。我的堂姐夫叫叶帆舟。” 我这样一说,罗克明同志接着说:“叶帆舟吗,是我在广州交游的朋友,经常过从,他是在广州搞军队的。是不是我们去访问他一下?” 我们就决定去访叶帆舟。分界到罗镜有十几里路程,问了一些人,才找到二姐家。问起二姐夫,她说已去广州多时,到现在还未回来,后来介绍我们去会见她家公,即叶帆舟的父亲,互相介绍过之后,他一听见是亲戚加朋友,就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经过接触倾谈,朱、罗两同志觉得叶老说话机智,对时局颇有见解,但可借叶帆舟不在家,便要告辞。叶老诚恳招待,并强为挽留。我们就在罗镜呆了几天,也了解了一些政治情况。这时我们离开怀乡已久,又没有交通员到这里来。 有一天叶老从街上匆匆回来,告诉我们:“此间风声鹤唉,草木皆兵,形势不妙,吾老矣,爱莫能助。”我们就离开罗镜了。 六、回榕垌 离开罗镜后,又去上赖。上赖是郁南县同信宜的平民乡交界的地方,比平民乡还高出好几百公尺,要经过马射尿那些地方上去。那里大概在明朝时是瑶人居住过的地方,近代以来没有人敢去那里居住。所谓马射尿就是那个瑶山(已忘记其名称)的小河和小湖泊流下平民乡的瀑布的形象性的地名,在它的旁边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到上赖。我们天微亮的时候从中伙出发,黄昏时才找到杨廷焕家。杨是我在榕垌小学的同学,又是信中的同班同学,他和我在班上演讲比赛是数一数二的。他是共青团员,因为我们在罗镜得知风声不好的形势,就想把朱、罗两同志暂住他家里,我先返家去,再同张信豪、张敏豪看看形势怎样,召集的帮会人物达到怎样的程度。他和他的父亲也很热情地招待我们。他和罗克明同志还有师生关系,第二天就杀鸡磨豆腐,饮酒,真是情至谊尽了。 我第三天从上赖回到榕垌,同杨叙庆、杨万禄研究一系列的问题,我先请杨叙庆去找张信豪来商量。我就在龙眼寨老家等他,杨叙庆刚从怀乡回来,杨廷焕又把朱、罗两同志送回到龙眼寨了。 那时我的家已经迁到亚鹩坪,在老屋这边我最亲的就是十四婶带儿子杨万汉,杨万汉那时还是十四、五岁左右。有些祖尝分给我的谷留在十四婶家里,我就自作主张,请十四婶帮我粜一些谷做菜金,磨谷整米做饭菜招待我这两位客人。杨万禄、杨叙庆也争着要招待他们。叙庆从怀乡回来说,找不到张敏豪他们两个,扑了一个空。 罗克明再写信叫杨叙庆去找他们。我们每日就在杨万清的客厅上讨论国家大事,争论得热哄哄的。当朱、罗问到我家邻近有哪些人物时,我说:“我们榕垌有什么人呢?龙眼寨有杨昆生,他是爱讲时务的。榕垌主要是杨泽庭,杨泽庭是有地位的,但也不得志,民国三年搞猪仔议员选举,做了陈铭盘的猪仔,失败了。现在是信宜县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新图局的局绅,又是榕小的校长。我那次在榕小演剧,杨泽庭对我不满,我不敢去看他。但对杨昆生我敢对他宣传的,通过杨昆生去拉杨泽庭是一个好方法。”于是朱、罗就叫我去找杨昆生谈。我去找杨昆生,谈及朱也赤,是问名的,罗克明是怀小的老师,都很尊重。我当时就对他首先讲革命形势,从先讲孙中山搞革命失败了十次以后,才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讲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再讲到我们共产党搞革命,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时,他敏感地问: “你想拉我做共产党吗?” “共产党不拉夫,这同蒋介石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不大相同。”我接着说,“共产党讲道理,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都很讲道理。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们是讲道德的,不是孔子的虚伪道德,是共产主义的道德。” 我又继续说:“你读很多书,对人讲很多故事,得人欣赏,也希望你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共产主义的书,学得更广一些。” 杨昆生说:“这样吧,明日晚上,请朱、罗两位先生来我家吃饭。今日我同你去拜访他们。 朱也赤 杨昆生是我的堂叔辈,他大我二十岁,平时我对他讲话,也是没有什么拘束的。于是我陪同他来看朱、罗同忠。杨昆生说话很投机,以学者的身份来看待他们俩人,米、多也以礼相待。罗克明大谈革命道理:中国很弱,成了东亚病夫,帝国主义虽没完全瓜分中国,但已把中国划分几个势力范围。如果不是苏联革命,不是中共的产生,不是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中国迟早是要被彻底瓜分的。你看五四、二七、五州、省港大罢工,不都是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者几个响亮的耳光吗!武汉、九江租界的收回,帝国主义者就惊慌失措。炮击南京威吓蒋介石。上海工人建立自己的政府,多么出色!但是蒋介石甘愿为虎作伥,屠杀工人农民、共产党人、革命的知识分子,甘愿做孙总理的叛徒,真是令人发指!怀乡暴动是配合广州暴动发动起来的,本来我们还没有准备得充分,形势逼得太紧,不得已而进行的,所以失败了。但革命是不怕失败的,有失败才会有成功。” 中杨昆生说:“今日聆听先生的高见,顿开茅塞。身处在穷乡僻壤。虽看报纸,略知时局的变化。但还没有听过你说的这番大道理,也增加了我的爱国心。” 朱也赤同志说:“刚才罗克明说及怀乡暴动与广州暴动,是形势逼迫使成。蒋介石不先向我们共产党开刀,我们就不会搞八一南昌暴动,汪精卫不同蒋介石同流合污,我们也不会搞广州暴动。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逼我们干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没有中共的诞生,就更不会有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孙总理干革命四十年,经过十次革命失败,才有辛亥革命的成就,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府,建立民国。后来让位给袁世凯,大权旁落,革命又遭失败。张勋、袁世凯倒了,陈炯明又炮击大元帅府。真是伤心惨目,有如是耶。但是孙总理还是硬着头皮,流血不流泪,要把中国搞好,认定唯一出路,就是三大政策,谁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北伐只打到长江中下游,蒋介石就背叛孙总理,屠杀共产党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姐妹?谁无夫妇?经此屠杀,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没有这么凄惨!到了今天,千百万人民,敢怒不敢言!怕什么?我就要说,蒋介石再派十万大军,我也要说。革命的人马,总是绝大多数的,反革命的人马,总是极少数的,历史总是见证人!" 朱也赤这样一讲,使杨昆生听得更是津津有味。他当即表示,明日早晨请到草舍一叙。到第二天去吃了午餐再留晚餐,又是鸡鸭鱼肉,烧酒饭菜,仿佛是酬劳了朱、罗昨日的一席话。 经过与杨昆生的谈话,我也转托他同杨泽庭谈谈,先试探他的态度,后来再问他是否跟朱,罗同志见面。杨昆生也很会兜圈子,对杨泽庭先说时局。后来我去问他,他说:“我不敢向他谈,但他好似已有点知道朱也赤和罗克明住在你老家了。” 罗克明 我想去找杨务英(泽庭的儿子),很快已经是春节了。朱、罗两同志急于叫我上云开找张凯如,把赤卫队组织起来。朱、罗等年卅晚留在亚鸡坪过年,年初一杨叙庆回来。"我于年初二起程去云开。除请十四婶和万汉(杨炳年的父亲)做好革命保姆和勤务兵以外,我就只身上云开。张凯如招待我住在云开小学。当晚他找到许多青少年来同我谈话,其中有一个住在张家对面的河坝铺的覃xx,他去过云南,年龄比较大,很同情革命,并愿参加我们的队伍。 我讲的话大多是朱也赤、罗克明同志近来对叶老和杨昆生讲话的大意,也讲了要宣传革命道理,争取群众,朋友愈多愈好,敌人越少越佳的意思。 我同张凯如说:“凡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都请他们参加我们的队伍。一是共青团,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二是少年先锋队,十二岁至十五岁,三是赤卫队,十五岁至卅岁都可以。有枪带枪,无枪带剑,入则为农,出则为军,一面种田,一面干革命。我们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凯如说:“可以带枪的有廿人左右。带剑的和带红樱枪的就多了。只要革命需要,一声号令,无不响应。如朱、罗两同志愿意来云开,我们可以留他们在这里做革命工作。” 覃xx说:“我家单独一幢屋,人口不多,如蒙朱、罗同毒来住,我们极为欢迎,我可以保证安全无事。我们有枪械。对面就是张凯如家,他们人多,出入不方便。” 七、朱也赤高开信宜 两天后我回到龙眼寨,杨叙庆告诉我:“杨昆生来讲,说是杨泽庭说的,县里有文件,要缉拿朱、罗等人,马上召集各局绅会议,阿昆说,希望是夜走上坑坪七哥那里,然后送他们到亚鹩坪。” 我赶快回亚鹩坪。朱、罗同志住在我家的阁楼,朱在看《向导》,罗在看《三国演义》,我首先汇报去云开情况,罗也讲了县里反革命的逆流就要到来。大家研究了如何应付时局。 朱说:“马上把黄佩兴(当地大地主)拿下来怎样?”我去找杨文豪、杨花旦都扑了空,再去牛蕴找丘华标也是扑了空。这时,杨叙庆带来了信,是广州湾的交通员送来的。朱也赤同志接信后,知道组织要他即日晚上去广州湾。临行前朱同志对罗说:“从今以后,信宜工作,全由你负责了。”当晚我送他到官渡头,我又赶回家来。 八、遇险 没有几天,张信豪来到我家,罗同志决定再去钱排、达垌,并要我一同去,带几十元钱。我说不如去云开。他们认为仍以钱排达垌为中心,他们一个先去了,我为了筹备几十元,还要等一些时日。过了几天,我们终于筹到三十元。我父亲有些懊恼,叫我去南洋干苦工,过一两年再回家。 我去达垌找到罗克明和张信豪,他们住在一户农家里,那人是帮会的头头,又是种田人。那时,钱排、达地风声也紧了,他叫我们不要到外面转,恐对我们不利。于是我们决定去云开找张凯如。达垌到云开要走几十里的路程。我带去的钱都用来交饮食了,大家身上没有什么钱了。去云开要经过竹垌,竹垌是共青团员孔昭然、孔昭俊的家乡。张信豪同他们是高州中学的侗学,而且很要好。但他知道孔昭然已去香港读书,只有孔昭俊还在家。我决定先去找他,然后再去云开。因为走了许多路,到竹垌的一间桥头铺,吃了几角钱米粉,那时准备找不到孔昭俊时,上云开还有一段很长的山岭要爬的。 到孔昭俊家,一面打门,一面叫孔昭俊。张信豪是来过他家的,确认是没有打错门。只见一个高大的中年人一开门,即匆匆忙忙的从扶梯走上楼,边走边说:没有此人。"我们大家便觉得有点惊异,当即决定上云开。吃那几角钱的米粉在爬上山路时,已觉得有点饿了,但总觉得找不到孔照俊,又遇着这样一个突兀的人,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虽然劳累也走得很快。到云开,已是黄昏的时候,我还认得河坝铺这幢房子,直接找到覃。我们刚想坐下来,突然有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入来对我打话。我在钱排、达调、云开都跟他们讲涯话,而罗、张他们不懂涯话,因为我同老覃的家属讲涯话,那两人认为我是本地人,就说:他们是朱也赤、罗克明,我们是来途捕他们的。你们不要让他们走。我们两个只各带剑仔一把。” 接着来了两个带驳壳的小青年,他们是张凯如派来的。他们悄悄对我说:我去同他们讲话,你们趁机从左边的门出去。”的确这个小青年在查问他们来意,等他们讲话时,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从张家的屋边,走上屋背。他们用怀乡白话对我们说: “不要怕,这里都是我们的防地,他们不敢来,来我们就打他。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我们去找张凯如来,准备请你们吃饭,并安排住宿。" 张信豪首先慌得面无人色。罗克明沉思着。我说:“这几个青年我都在云开见过面,但都叫不出名字来。的确是我们的人。” 张信豪说:“我们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我说:“我们已经跑了几十里路,在竹垌只吃了一点米粉,现在肚子也饿了,还走到那里去呢?” 张信豪一面跑一面说:“不管跑到那里,离敌人相反的方向跑。" 罗克明说:"如果我有驳壳在手,我就打死他们两个。”我说:“我们这样不是把事情闹僵了吗?擒贼必须擒王。我主张回去找张凯如商量如何应付这紧急形势。” 突然,“丢那妈,放他们跑掉啦!”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鼓。 我说:“不要怕,不要走,越走越危险,人生地疏,怎可以乱跑呢!干革命,就要碰到敌人,要临机应变。” 张信豪气喘地对我说:"怎样临机应变呢?" 我说:“同张凯如商量,估计敌我的力量对比如何,我们抄他们靶子,可以一网打尽就一网打尽他们。” “别多议论,跑出危险地带再说”罗克明说。 于是我们跑了约莫个把钟头,乘着月光爬上龙须顶,那里是没有人烟的地带。我说:“现在应该决定走的目的地。 回榕垌的路途我很熟悉,但杨泽庭已通知我们离开,恐怕会遇着敌人。回达垌呢,我们不能从原路回去,回去更会遇着孔家大敌。那么我们先下山去,乘月光看山花,可以走牛垌的山边到扶曹去,从扶曹再回钱排,但是我们这么饥饿,怎么吃得消呢?去扶曹也有困难,要找到扶曹的高桥才能渡河。” 罗克明说:“就照你的计划走。”这时我才发现罗克明丢了一只鞋,也不吱声,我要脱我的鞋给他穿,他坚决不要。走了这么多的路,他的脚皮也磨得很痛了。我们就走下坡,从右边的山脉朝扶曹的方向行。到了扶曹河,水流较急,但不深,我找到一条木棍,试探了水的深度,我说:“水不深,就从这里过去。”这次总算安全渡过了。但我们都非常饥饿和疲劳,行了一段路,遇到一条用旧棺材板做的小桥,我就躺在那里睡了一阵,又来劲了。又走了一阵,到扶曹了,太饿了。我去摘农民的芥菜吃,太辣了,吃不下。摘了苦脉菜吃,还可口。摘了一些到小溪去洗洗搓搓才吃,的确渡过了饥饿关。因为我会讲涯话,就到一个人家去求乞他们给我一些东西,没有人回答,又去另一家,有回答了:“不要再叫了,等一会我放狗吠你(土话,放狗吠是开枪)。”这样,依然挨着饿又爬过山,山过山,坳过坳。碰着有酸醋藤的叶也摘来吃。将到钱排时,路边有一家小商店,我敲窗门,说:“买饼仔。”果然得心应手,店里人点了灯说:“你盖好屋了,回家了?”大约店主人认错了人,我说:“是。”买了四角钱饼仔,我们几个人大吃一顿,又有力气了。 到天刚亮的时候,找到了罗克明同志热悉的一个战友,家里姓什么也忘记了。“你们从那里来?”东道主说,“前晚孔少华到邻村说,要通维米也赤、罗克明,叫大家警惕,还要搞十家联结。我们这里还没有人来说。”我们也对他讲了孔少华派民团跟踪的情况。 他很快就备好早饭给我们吃。他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农民发动不起来,趁着没人注意,你们还是去达垌。 在达垌住某农家。对他们讲了竹垌孔少华派民团追踪,我们突围的遭遇。主人说:"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神不惊,鬼不怕,官兵来到也得下马。” 杨叙庆也特来找我们,要我们住得秘密,暂时不要跟人来往。而且各自分居,不要聚集在一起。杨万禄又带来一支我托他带来的手枪。由十五姑爷(姓名都忘记了)安排我和万禄到一家农业兼种茶的人家居住。我们两个各给他几元钱一个月,就住上了两个月。住在牛栏棚上,起初那些牛的气味真是难闻,但后来也习惯了。后来十五姑爷通知我和万禄回家,由表弟带路,经过一个大山才到十五姑爷的家。此时,罗克明到香港去了。 度过这一个难关,将要回到坑评七叔那里时,经过杨xx(花名“老虎四”)的家,已天亮了,他认得我们,马上就去报告杨泽庭。到七叔那里,吃了早餐,就回我家去了。我们两个住在阎楼。我的老婆丘国英抱着一个初生没有多久的小儿一早来就见我,说:“辛苦了吧,公公说,"当你没有了”就留下这个儿子,是不幸中的幸事。”我接过儿子,我老婆的眼泪就滚滚的流下来。 (九)在香港 回到亚鹤坪后,父亲对我说:“杨诚轩说你们带领大批共产党的红军回来,这里大搞十家联结。”杨诚轩是同我父亲很好交请的乡长,叫父亲不要让那些人到我家,万元、万禄也得躲避风头。 我们回到家,父亲当即带我到大坪阿韦五的家去躲避。又遇他老妻死后做七,带我们去瓦窑住了两天。白天小孩放牛,看见我们在窑里挂的手巾,就用石头掷进米,杨万禄就即刻举起手枪来,我一手拨开。后来才知道就是阿韦五的小女,吓走了那几个孩子,说是有鬼。如果不是我拦住万禄的枪,恐怕要出事故了。 革命工作展不开,反而要逃避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保甲制度的十家联结,的确是反动透顶了。蒋介石就利用这些保甲制度作为乡村统治的武器,地主阶级就是他的统治基础。 万禄到底还有一些办法。他的岳丈叫阿彭公,姓李,是佛水地方有名的捞家头。万禄就带我们到那里去住。他的伍是李xx(小名李阿九),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带来一些小说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他的一阁楼,并不出入,晚上下来厅间聊天。有一晚有一个剪发的小伙子来找万禄的小舅,突然见我就惊奇起来。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去容县他的亲戚那里住了一个时候。 两个月后,我们收到罗克明同志的信。他们都去澳门、香港了,邀我们法。我父亲和万禄的祖母筹得了百多元,于打万属我们去南洋到橡胶,当工人。 我们回到佛水,住在阿彭公家两天,就起程去澳门。从佛水出发,日行百里,走了四天,经过岑溪、藤县到达梧州。那时已是六月天,戴着竹叶帽,从藤县搭小汽船到梧州时,过往人都叫我把竹叶帽摔了,我们还舍不得。到梧州住一问最蹩脚的旅舍,是用板壁隔的。出去逛梧州市,街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番摊馆(赌博场)和卖鸦片泥的馆子。我由于多日来劳累,蚊子叮,发高烧。去信澳门,罗克明已复信来,我就带病去香港转搭澳门的轮船,找到罗克明同志。 罗克明同志对我们说明目前的国内外政治形势,说党的革命事业前途光明。在澳门住了许多天,他叫我去香港广东省委里做工作,万禄暂留澳门或去南洋工作。 在香港先住在团省委招待所,我的发烧时好时坏,人也消瘦了。招待所里同志都叫我去“医院”免费就诊。有人叫我住院,有人说,不行。入院不许转院,一是活着出院,二是死了出院。最后还是省委的西医给我治好,说是打摆子,服奎宁就好了。在招待所里我认识车振轮(茂名人)、阳洁明和阳xx夫妇(广西人)。病好了,省委叫我在秘书处工作,张敏豪就在那里刻钢版,印《劳动周刊》。一个女同志,大家叫她的小名“屈尾龙”,每天做学生打扮,提着一个书篮上街,负责收从上海党中央寄来的文件,收到后用碘酒一涂就认出来了。涂好我就抄,有时也来不及抄,就带出去了。过了一个时候,又叫我去省委住的住宅去住,一个姓吴的夫妇两人住在那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听说朱也赤也来香港,但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有一次有人说要调我去新会等地当小学教师,但没有调去。后来决定调我去广州湾,我想一定是朱也赤提出的意见。于是我又去招待所等候。那时住在湾仔大道东一间药店的四楼上。招待所人事往来的确很多。住在招待所有李海筹(省委,是海员)、丘九(丘化名,原名忘记了)、陆毅超(女,广西容县人)、符德谦、符明彝、李xx(叫细佬哥,年龄最小)他们三人都是海南岛文昌人,还有一个朱xx(潮汕或梅县人,讲客家话)。省委经常来招待所开会。我看见一次恽代英同志在出席省委会议,他穿着一件长衫,是教授的打扮。为了携带文件,我准备了一个藤箱,加一层薄板,再糊上木箱纸,上船下船,一般是检查不出来的。 这时,我突然患了痢疾,何时出发去广州湾,我请示过省委,批复说等你好了以后再去。不久得到消息说朱也赤同志和在广州湾工作的同志全部被捕。这个不幸消息传来,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一连几日都睡不好觉,病愁交加,真是最沉痛的事情! 十、驱逐出境 一九二九年元旦,约在凌晨二时,突然有人敲门,越敲越急,后来不但是谁开了门。闯入来的是一批香港的警察,有英国人也有华人。我和朱xx共铺,是在后房,丘九和李海筹住在第二间后房,其余的住在厅间。丘九说:“我在这个小旅馆做厨工的。老板回家了。”问其他的说是住客,我说:“准备去南洋做工,那里有亲戚朋友。”他们在拼命搜我们的行李。 这些警察不问青红皂白,一个个用手铐铐住,押我们下楼,押上黑囚车,到警察局,临时押在广场。不久共青团中央委员刘立群夫妇俩和九龙区团委书记郑子初、某工厂李xx也押到了,共约十六人。郑子初只有十五六岁,特警把他的头发抓住向天空一提就提起来了,大家都愤怒得要命,心里都骂他们是狗,后来才知道这个特警是海陆丰人,他恨彭湃同志,今天他就向我们报复,发泄他的阶级仇恨。 当晚我们被押入警局的拘留所,是大铺,有二十几人。马桶也在里面。屎尿臭味熏天,虱子也很多。押了一晚,就送到维多利亚拘留所。这个拘留所是一幢大洋房,有三层楼。每人一间小房,三张毯子,一个马桶,一个痰桶。门上有个手指这么大的喇叭式的垌,以便狱卒检查在押人员的情况。门底有一条三寸高的缝,以备囚人饭菜、马桶、痰盅从那里送出送入,以及晚上早晨三张毯子传入传出。毯子都有虱子,我们睡觉都剥光衣服,以免走上自己的衣服。每星期日开放我们出来在走廊上擦马桶,丘九和细佬哥(李xx)做服役人员。晚上我们唱起国际歌,被锁鬼知道了,分别殴打我们。刘立群住在楼下,当他是政治犯看待,给他睡铁床。陆毅超和刘立群的爱人住在一起,后来陆毅超疯了。得到消息以后,我们都为她担忧。 省委济难会一个姓陈的同志给我们十六人聘请香港名律师辩护。大约拘押了三个月左右,我们十六人被告为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嫌疑犯,一律驱逐出境十年。我和郑子初驱逐往江门,刘立群夫妇、丘九、李海筹被驱往上海。其余各自驱逐回原籍。但不准驱逐到外国。我被传去警局的办公室问过一次话,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或共青团员,我都否认。其余的同志也是传问过一次。总之,干钧之力就是罗文锦律师。出狱前,我和丘九也交换了通信地址,我打算到江门以后,再回澳门,再找罗克明同志。 团组织派郑子初的母亲护送我们去江门,转澳门,然后她回中山家乡。郑子初原来在香港马玉糖果厂做工人。我们到江门旅馆住,警察来查我们时,郑母日认我是她的大儿子,子初是她的二儿子。我们被押送上船,还是我们两人铐着手铐,等到船要开了,才把手铐开掉。此外还给我们各人一张驱逐出境的证明纸,以便过境时可以在香港逗留二十四小时。郑母把我们的这证明书撕掉扔到海里了。 我到澳门,适遇罗克明、张信豪、杨万禄都聚在那里。张信豪因为我被捕,就离开革命岗位了。张敏豪也在香港华南日报当校对员了。杨万禄上次去南洋去不成又回家乡去。我写信给父亲,说明我在港被捕,不久可以出狱,父亲又寿了五十元交杨万禄带给我,叮咛我一定要去南洋当工人。而罗克明却鼓励我去上海读书。我们在澳门住了几十日,万禄带来的钱花光了,去南洋的旅费也不够了。回到家后,知道乡间的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我和万禄、叙庆、万清、六伯的屋都被军队来钉封,没有门口出入。后来邻居的人教我们家人,另外满开门口出入。杨万禄去南洋以后,罗克明还在澳门和河内之间来往。不久罗克明也到新加坡了。他还和我通信,万禄在橡树园做苦工,得到的工钱节约出来给罗干革命。罗在那里办了一个报纸,后来被捕,也被驱逐出境,以后在越南和广西左右江之间来往做革命工作。那时候汪精卫派的俞作柏的部队就在南宁一带有统治力量,中共就派很多人员在那里工作,罗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干革命的。 我回到家以后,还是偷偷地在阁楼上。父亲对我说:“我被迫交悬赏通缉你的几百元。”父亲就卖掉自置的榕垌黄镇坑的九担租的田,又标了一个会,都为我花光了。一九三〇年我到上海考进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学系。在上海还保持同罗克明通信,那时他还在新加坡干革命。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战役后,我回广州,又考入中山大学社会系。这时候接张敏豪来信,叫我即日去香港,同罗克明会晤,否期将来很难见到他了。我还以为他将出国了。我因被驱逐出境,一则不宜去香港,二则无旅费,我不知道他为革命积劳成疾,由战地来港就医,病危由张敏豪写信给我。谁知罗克明同志就这样病逝香港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香港南华日报工作,黄折冲编辑对我说过:“罗克明在香港府逝,张敏豪葬他在九龙,后来张敏豪又病逝了,我们又把他葬在罗克明的坟旁,都立了墓碑。”我曾去凭吊他们的墓地,不胜感慨,说不尽的悲痛。我因而回忆起罗克明同志写给我的一首诗《希望》,我只记得起头一句:“倘若我没有你时,我将……”,共有四段都是这样开头的,内容是抒发胸怀壮志豪情的抒情诗。他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我们在云开突围时,一出门口过河,他就掉了一只鞋,他赤着脚跑百里夜路,忍饥挨寒,就够做我们的老师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东奔西跑,兢兢业业,先来往于香港、澳门、越南,后去新加坡办报,被捕入狱,被驱逐出境,后又来往于广西左右江与越南之间,积劳成疾,香港就医,终于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岁而已。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南京 选自《信宜党史》第一辑:P-P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13801256026.com/pgst/pgst/1261.html |
当前位置: 信宜 >信宜党史第一辑选文怀乡起义前后的回忆
时间:2022/8/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大手笔茂名12大生态文旅项目来袭你的
- 下一篇文章: 也谈粤语的传承问题